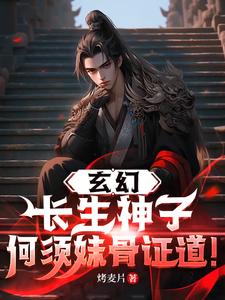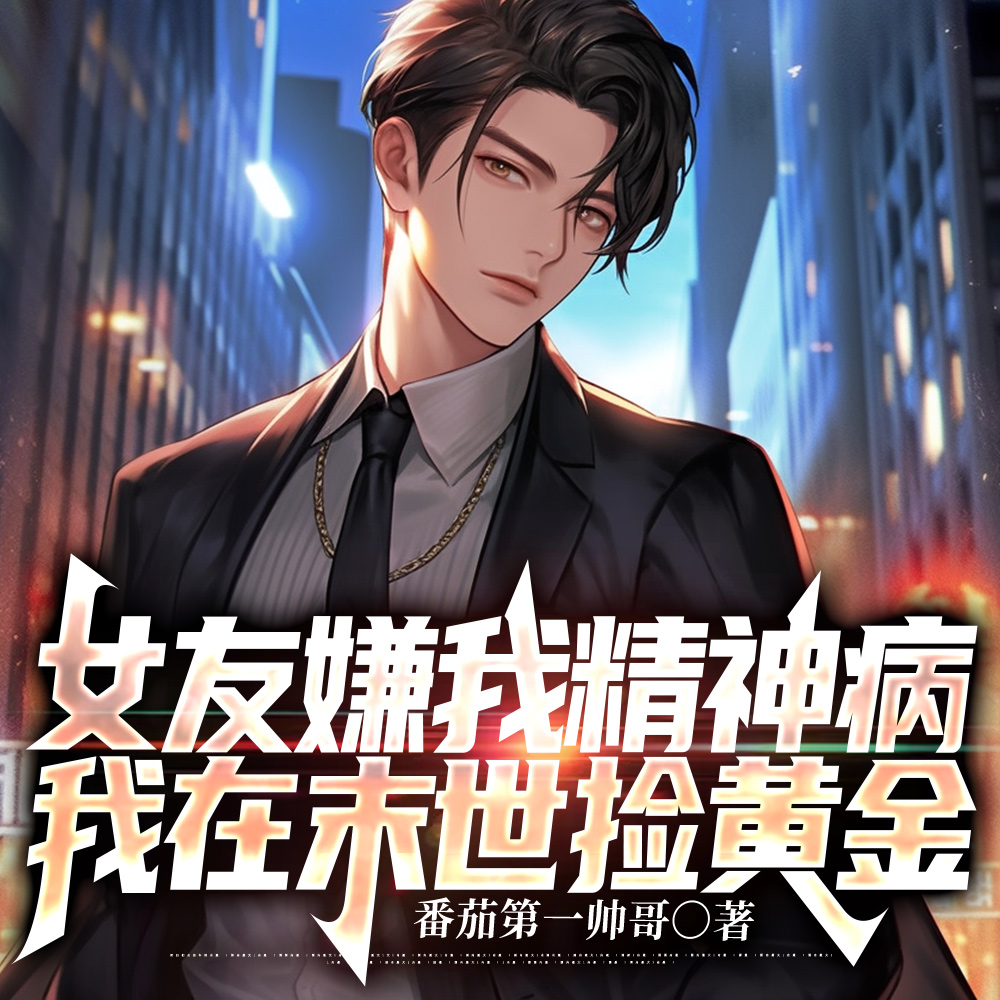杨炯在营台上伫立良久,眼见潘简若已将一千金花卫整饬停当,当下再不耽搁,即刻点兵向南折返,往大华而去。
但见马蹄踏踏,烟尘滚滚,一千金花卫旌旗招展,星夜兼程,过得真定府,于一日正午时分才入太原府城。
待城门在望,早见太原知府已率一干属吏候在道旁。
那知府见大军到来,忙趋步上前,躬身行礼道:“下官太原知府褚安民,见过……”
杨炯忙翻身下马,抢步上前将这鬓发花白的师兄搀住,半嗔半笑道:“储师兄这是成心让我难堪不是?您老眼看就到花甲之年,比家父还长着几岁,若是让他老人家知道您给我行此大礼,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呀!”
褚安民面色一肃,沉声道:“师弟这说的是哪里话!你如今是当朝实打实的侯爷,此番征战更是为大华谋得十年安稳,莫说我行个礼,便是满朝文武列队相迎也不为过。想我本是一介都进奏官,若非恩师提携,哪有今日?数十年案牍劳形,这份知遇之恩岂敢相忘?”
说着又要俯身行礼。
杨炯早知这褚师兄的倔脾气,当下忙侧身闪至一旁,既不落他礼数,又将这一拜虚引向身后一干金花卫。
待褚安民礼毕,方笑着将他搀起,朝身后一众太原府属官挥了挥手,朗声道:“都散了吧!我最不喜这些虚礼,诸位且去安排驻军事宜,各忙各的便是!”
众官员面面相觑,原都巴望着在镇南侯跟前露个脸儿,最不济混个脸熟也好。全国谁不知当今梁王看重的人,升迁的速度比那燎原之火还要迅猛,哪个能不眼红?
单说这新上任的褚府尹便是现成的例子:一个在进奏院理了数十年奏折的都进奏官,不过因送折时与左相攀谈几句,便被外放做了知县,短短十载竟已历两府,如今更是坐镇边陲的封疆大吏。
人生能有几回这般际遇?坊间都传镇南侯用人不拘一格,单是西夏一战,受封的大将军便快赶上开国时的阵仗。众人岂肯错过这等良机?当下忙凑将上来,你一言我一语,皆是些奉承话。
杨炯听着这些言不由衷的话语,只觉浑身难受,当即心中一转,便抬手虚按,示意众人噤声。
随即将潘简若与卢和铃唤至近前,笑着向褚安民引荐:“师兄,这位是拙荆,长安潘氏千金。”
潘简若款步上前,盈盈一礼,风姿绰约:“师兄安好。”
褚安民见状,忙不迭拱手回礼,口中连道:“哎呀!可是金花卫潘帅的掌上明珠?老夫如何受得起真将军的礼数!”
“师兄忒也见外了,自家人哪论这些!” 潘简若言笑晏晏,礼毕便轻移莲步,退至杨炯身侧。
杨炯清了清嗓子,特意抬高声调,又引过卢和铃道:“师兄再看,这位亦是内人,范阳卢氏女。她常住太原府,往后还请师兄多多照拂才是。”
褚安民尚未及言,身后一众官员早七嘴八舌抢着应和。
一属官堆起满脸笑纹,忙不迭道:“侯爷这话忒见外了!太原府谁人不识卢夫人的尊容?往后夫人但有差遣,小的们跑腿儿都嫌慢呢!”
话音未落,一员面相憨厚的武将已扯开嗓子嚷道:“侯爷只管把心揣回肚里!有俺牛三在,定保夫人周全,若有半分闪失,俺提头来见!” 说罢还重重拍了拍胸脯,生怕杨炯漏了他的名字。
其余官吏见状,纷纷效仿,一时喊名表忠之声此起彼伏。
杨炯冷眼瞧着这出热闹戏码,心下暗忖:官场这大染缸,若事事较真,倒真就无人可用了。
念及此,杨炯面上已堆起笑意,抬手虚按道:“诸位美意本侯记下了,眼见日头将沉,且先安置驻军要紧。”
众官吏在宦海沉浮数十载,岂有不明白的?皆知卢夫人这一出,名为 “照拂”,实则是镇南侯给众人指了条攀附的明路。
既已得了要领,再纠缠反显愚钝,当下纷纷拱手告退,簇拥着潘简若与金花卫进入城中。
褚安民与杨炯并辔而行,苦笑着摇头叹道:“师弟莫怪这些同僚。太原地处边隅,他们终年困在此处,盼个上进也是人之常情。他们其中不乏干练之才,只是久在这官场泥沼里打滚,难免沾些习气。这滋味,愚兄深有体会。” 说罢抚了抚鬓角霜白,眉间似有几分自嘲之意。
杨炯闻言,唇角微扬,打趣道:“褚师兄这做派,与当年在进奏院判若两人呢。”
褚安民摇了摇手,鬓边白发随动作轻晃:“你当我愿这般?早年埋头案牍,单是各府县奏折分类排序便忙得脚不沾地,哪有空琢磨这些人情世故?若不是那日给恩师送折时得了机缘,怕真是要老死在那堆文书里了。”
杨炯对这位师兄印象颇深,老爷子书信里倒是着重提过,此人品性端方,于权位向无贪念,偏生记性惊人。近三年奏折能一字不差复述,五年内的也能道出梗概。这般 “活典籍” 本是入中枢做舍人的上佳人选,却因淡泊名利反被埋没。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