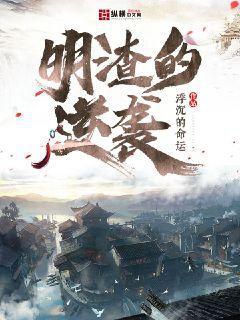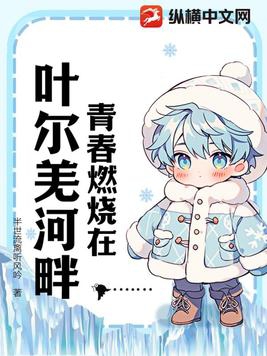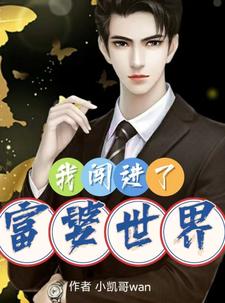镇江,京杭大运河江南段,也是大运河江南段和长江的交汇处,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,江南米粮赋税通过运河与长江南上北下,占领了这里,就切断了江南财赋北上之路,地理位置极其险要。
阳光炽热,芦苇轻拂,水面波光粼粼。
西津渡,镇江水师驻地,岸边一艘战船上,新任的镇江水师总兵施琅站在船头,正在看着水面上的镇江水师们操练,却似乎魂游天外。
要是当日没有执意杀了曾德,现在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?
数十年来,尤其是近些年来,这份懊悔一直伴随在施琅的心头。
少时学书不成,弃武从文,转眼韶华已逝,如今年过半百,两鬓斑白。
清顺治三年,随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降清。
顺治五年,走投无路,投入郑成功麾下,屡立战功。
顺治九年,受施琅节制的部将曾德为求出人头地,投入郑成功营中充当亲随。施琅听到消息后,大为愤慨,派人把曾德捉回斩首。郑成功驰令勿杀,施琅却悍然不顾,将曾德斩杀。
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氏旧将,断定他反形已露,将施琅、施琅之弟施显、施琅父亲施大宣拘捕。施琅逃到大陆。郑成功得知施琅逃入满清,将施大宣、施显处斩。
施琅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,对郑成功恨之入骨,死心塌地投靠清廷,一意同郑氏为敌。
自投清以来,施琅先后担任副将、总兵、水师提督等,参与清军对台湾郑氏的进攻和招抚。
康熙七年,清廷遣使赴台招抚失败后,施琅即上《边患宜靖疏》,次年又上《尽陈所见疏》,强调不能容许郑氏盘踞台湾,议谏被束之高阁。迁界令下,留京宿卫,长达七年。在京之日,甚为贫苦,依靠妻子在北京当女红裁缝贴补家用所需。施琅蛰伏待机,每日在府内耐心等待朝廷起用。
康熙十五年,八月初,浙江反叛,东南岌岌可危,在黄锡衮陈廷敬等大臣的力荐下,让他挂江南水师提督衔,任镇江水师总兵。
出任镇江水师总兵,虽然官职上并没有提升,甚至不升反降,但不失为一个好的复出迹象。
对于施琅来说,羁旅京城,南方不断传来的反叛军情,让他心情沉闷,度日如年。
离京之前,皇上殷殷叮嘱,海阔天空,施琅壮志踌躇,誓要立下一番功业。只要稳定了东南半壁,便可让朝廷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。除了吴三桂,才有可能促使朝廷出兵,平定台湾。
到了镇江,未能看到台湾或福建的战船北上,施琅也能腾出手来,操练水师。至于占据大半个浙江的王和垚部叛军,他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目光扫向运河西岸,水师营地以西的银山要塞,山上山下有两千余绿营兵驻守,旌旗飘飘。
永历十三年,郑成功北伐,清将管效忠带一万多大军驻守于银山,被郑成功的铁人军击溃,死伤无数。台湾郑氏虽然大不如前,但就凭这两千兵马,能防得了谁?
至于运河西岸的镇江城,里面有两千旗兵驻守,城墙上的炮口张大着嘴,像是食人的猛兽。
十几年没有战事,那些个铁疙瘩,还能用吗?
再看向运河东岸的圌山炮台,二十多门巨大的红衣火炮盘踞其上,直对长江江面,似乎威风凛凛。那是为进入长江、攻打南京的台湾郑氏准备。
台湾郑氏,郑成功已经死了,如今是他的儿子当权,报仇的意愿,似乎也没有那么强烈了。
当日,他要是不强行斩杀曾德,郑成功也不会杀了他的父亲与弟弟吧……
亲人的血海深仇,他能报吗?
“这兵,还得练啊!”
心思回到操练的水师身上,施琅轻轻摇了摇头。
就这些乌合之众,能经得起台湾郑氏的水师攻打吗?
郑氏陆战不行,朝廷不重视水师,什么时候,他才有机会组建水师,报仇雪恨啊?
看了看汗流浃背,狼狈不堪的水师士卒,再看了看日头,施琅轻轻摇了摇头。
“收兵!”
按他以前练兵,比这更热的日头,照练不误。但时过境迁,自己新来乍到,还要拉拢军心,不能硬来。
在京城待了七年,磨炼了他急躁的性子,也让他知道,有些事情,不能操之过急。就比如这练兵,即便他把兵练得再好,朝廷会立刻出兵吗?
以如今的战事情形来看,会不会攻台都不一定。
“父亲,听闻李之芳的女儿李若男与浙江叛军贼首王和垚有些瓜葛。李若男关押在南京,浙江叛军会北上攻打南京城吗?”
次子施世纶追随着父亲,一边往岸上走,一边问道。
施琅有八个儿子,长子施世泽过继给施琅亡兄施肇科为嗣子,在京城当个小官。此次南下,次子施世纶已经成人,精明强干,随他一同前往。至于他的其他六个儿子和妻妾,则是作为质子,都留在了京城。
“你是担心叛军北上,攻打镇江吧。”
施琅摇摇头:“我也不知道。前几日苏州传来的军情,浙江叛军在苏州与浙江边界上耀武扬威,似乎要攻打苏州。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