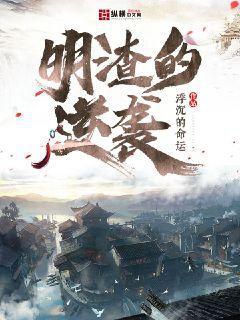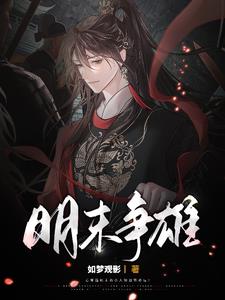银钱为庶政根本。
自义军入南京城,接受了原南京城的府库,所得纹银六十余万两,铜钱三四百万,但其所得税赋,大都来自于施行仅仅三四个月的盐课,不过十余万两,于总督府庞大的度之而言,杯水车薪。
没有大量的矿藏,没有煤铁,没有工商业,总督府赋税来源,少之又少。
总督府大堂上,朱和垚看着眼前江南士林的捐赠清单,轻声笑了起来。
南京王家,捐银三万两。
南京陆家,捐银三万两。
海宁陈家,捐银三万两。
苏州贝家,捐银五万两。
苏州毛家,捐银三万两。
苏州毕家,捐银三万两。
无锡许家,捐银三万两。
锡山秦家,捐银三万两。
………………
至于后面捐银万两,数千两者密密麻麻,不计其数。
捐银超过了两百万两!
雪中送炭,远胜于锦上添花。
江南士族之富裕,可见一斑。
“李大人,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啊!”
朱和垚放下清单,哈哈笑了起来。
杭州黄家,捐银五万两,或许是因为黄家人黄锡衮为当朝汉兵部尚书的缘故,也可能是因为黄家已经投诚于南京总督府。
杭州洪家,捐银三万两,黄洪一家,一荣俱荣,藕断丝连。
昆山徐家,一状元二探花,捐银三万两,其中缘由,不言而喻。
昆山顾家,捐银三万两。
昆山顾家,顾炎武的家族,捐银的却是与顾炎武不睦的顾氏家族。
李之芳满面红光,神色中却有不甘:“恩威兼施,报纸上痛斥,下官再敲打敲打。不过只有两百万两,还是比估计的五百万两少上许多。”
江南鱼米之乡,豪族大户数不胜数,一番恩威兼施威逼利诱下,只是诈出了两百万两,实在有些不满意。
“五百万两!”
朱和垚吃惊于“准岳父”的贪婪,笑声立刻中断,随即摇了摇头。
“李大人,我知道你是干吏,但凡事不能太简单粗暴,要循序渐进,不可操之过急。”
他的“岳父”,心狠手辣,精明强干,简直是个——狗官!
舆论之下,江南士林不得不掏银子出来,看似向总督府示好,实则是为了挽回脸面。
人性,果然经不起推敲。
李之芳讪讪一笑,很是满意“女婿”的赞赏。
能被“女婿”称赞,可是不容易。
朱和垚看了看一旁面色尴尬的黄宗羲与顾炎武,心头明白了几分。
“甲申年,崇祯帝欲调吴三桂关宁军禁卫北京,所需军饷仅仅 100万两纹银。崇祯帝囊中羞涩,内帑只存几万两银子。崇祯帝让群臣筹银,只得捐银二十余万两,调兵不得不作罢,大明无力回天。”
“崇祯帝煤山自缢,李自成入京,追赃助饷,仅仅十余日,所得 7000万两。大明士大夫,忠孝节义,为国为民,让人叹为观止。”
朱和垚看着神情黯然的黄顾几人,正色道:“几位先生,如果这两百万两银子,能够助我义军恢复汉家江山,能复我汉家衣冠,便是值得。”
黄顾二人都是肃然,大明亡了天下,士大夫功不可没。如今江南士林只捐了两百万两银子,还是国事,总督府得之,堂堂正正。
“大人,只要能击退来犯的清军,将来发行国债,便会要顺畅许多。”
黄宗羲未雨绸缪。
李之芳却是皱眉:“徐乾学传来消息,玄烨要御驾亲征,到时必会有数万甚至十万兵马。大人可要做好打算啊!”
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大外甥,捐银的同时,捎来书信,清廷会挥兵南下。
“李大人所言极是。虽说我江南义军善战,但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大人还是要早做打算,不可懈怠。”
顾炎武跟着说道。
朱和垚点点头,精神一振。
玄烨御驾亲征,来的正是时候。
自破了南京城,他就一直在厉兵秣马,积蓄力量,一刻不敢怠慢,就是为了应付将来的大战。
只要击溃了玄烨的大军,天下的攻守大势,就朝义军这一方倾斜了。
“大人,由于南京的战事,今年的秋赋还没有征收。地方府县,已经征了少许,不过都没有解运。还要不要继续征收?”
黄宗羲问道。
“不用了,已经征收的退回去,今岁不征赋税,明年再继续征收。”
朱和垚犹豫了一下,做了决断。
义军破了南京城,所获粮草辎重颇丰,撑到明夏没有问题。
今年的秋赋,就当给江南百姓的见面礼吧。
黄宗羲与顾炎武下去,李之芳却留了下来。
“李大人,有事吗?”
朱和垚放下手上的清单,好奇地问道。
李之芳两鬓平添了许多白发,看来公事上辛苦,不知道是不是乐在其中。
“大人,你和若男之间,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”
李之芳小心翼翼问道。
自从女儿被营救后,李若男多在杭州与苏州,与朱和垚聚少离多。他心里嘀咕着,莫不是二者之间,出了什么隔阂?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