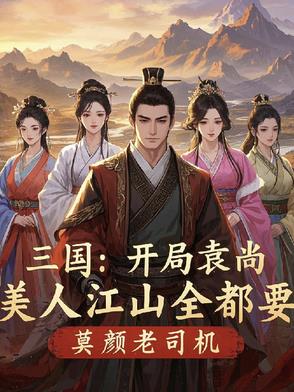第176章 洛阳纸短佳人启,邺城窑新水泥成
洛阳的秋风已带上几分凉意,卷起街边的落叶。
侍女轻步入内,低声道:“公主,冀州王越统领求见,说是侯爷有信至。”
端坐窗前,正翻阅书卷的万年公主刘婉,指尖微顿。她抬起头,面上平静无波,只眸光轻闪了一下。
“请他进来。”声音清越,带着皇家的雍容。
不多时,一身劲装的王越步入厅堂,躬身行礼:“末将王越,奉安平侯之命,参见公主殿下。此为侯爷亲笔书信。”
他双手呈上一封封缄完好的信件。
刘婉示意侍女接过,挥手道:“王统领一路辛苦,先下去歇息吧。”
“谢公主。”王越干脆利落地退下。
侍女将信奉上,刘婉接过,指腹轻轻摩挲着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,心中微澜。
她屏退左右,独自回到内室,坐在妆台前,这才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。
信纸展开,墨香混合着远方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字里行间,是袁尚对冀州近况的简述,提及改革的种种不易,言辞间却透着一股蓬勃的锐气。
然而,读到后面,笔锋渐转柔和。他写到洛阳一别,相思之苦,写到冀州局势初定却仍暗流涌动,无法即刻迎她北上的歉疚与无奈。字句间那份深藏的愧疚与浓浓的思念,几乎要透过纸背,灼痛她的心。
夫君…… 刘婉心中轻叹。她何尝不知他的难处。身处洛阳,虽有父皇庇护,但朝堂诡谲,她亦是步步谨慎。冀州是他立足之本,更是未来根基,岂能因儿女情长而有半分懈怠。
只是,夜深人静之时,那份独守空闺的落寞与对夫君的期盼,又岂是三言两语能道尽。她盼着他能披荆斩棘,成就大业,也盼着能早日相聚,不再两地分离。
她将信纸反复看了几遍,仿佛要将那字迹刻入心底。
许久,刘婉才将信纸小心折好,贴身收起。
心中千回百转,最终化为一缕轻烟般的叹息。
她走到妆台前,取过早已备好的笔墨纸砚。纤纤素手研墨,心思沉静下来。
片刻后,她提笔蘸墨,在素白的纸笺上写下回信。信中并未多言洛阳琐事,只殷殷嘱咐他冀州天寒,务必保重身体,勿因政务操劳过度。又提及冀州新政广受关注,望他稳步推行,凡事三思而后行。字里行间,是妻子对丈夫最真切的关怀与期盼,却无半分小儿女的痴缠埋怨。
写毕,仔细封好,她扬声道:“来人。”
侍女应声而入。
“传王越统领。”
不多时,王越再次步入殿内,躬身行礼:“公主殿下有何吩咐?”
刘婉将手中封好的信递给侍女,示意转交给王越。“王统领,这是本宫的回信,劳烦你带回冀州,亲手交予侯爷。”
王越双手接过,郑重道:“末将遵命!定不负公主所托。”
刘婉微微颔首,语气温和了几分:“此去路途遥远,你也需多保重。替本宫转告侯爷,万事以大局为重,亦需顾惜自身。”
“谢公主关怀,末将谨记。”王越再次行礼,随后转身,领着信件,大步离开了。
稍作休整,第二日王越一行人离开了安平侯府,向城南蔡府方向行去。
蔡府门前,绿珠正踮着脚尖张望,见到王越一行人靠近,连忙转身跑进院内:“小姐,小姐,好像是冀州来人了!”
书房内,蔡琰正临窗抚琴,闻言琴音微顿,随即恢复流畅。片刻后,绿珠引着王越入内。王越躬身行礼,动作干练:“末将王越,奉安平侯之命,拜见蔡小姐。”他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,双手奉上,“此乃侯爷亲笔,请小姐过目。”
蔡琰起身,素手接过。信封上的字迹刚劲有力,正是她记忆中的模样。屏退绿珠,她回到案前,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。
信中,袁尚先是问候了蔡邕与她的近况,随后便言辞恳切,提及昔日在蔡府的琴音之约,以及后来许下的承诺。如今冀州初定,百废待兴,他诚邀蔡琰前往邺城,共同见证冀州的变革,也希望她能以其才学,为冀州文化教化贡献一份力量。信末,更是隐晦地提及,邺城已备好清静雅致的院落,静候佳人。
指尖抚过那些熟悉的字迹,蔡琰的心湖泛起层层涟漪。那日在蔡府的《十面埋伏》与《女儿情》,那夜宴上的“醉卧沙场君莫笑”,一幕幕涌上心头。父亲的嘱托,袁尚的风采,冀州的勃勃生机…这一切都让她心生向往。可离别故土,远赴一个已有数位佳人的侯府,前路充满了未知,又让她生出一丝难言的惆怅与不安。她将信纸轻轻折好,放在琴旁,久久伫立窗前,望着庭院中开始泛黄的梧桐叶。
当夜,书房灯火通明。蔡邕看着女儿带回的书信,捻须沉吟良久。
“琰儿,袁显甫此人,雄才大略,观其在冀幽所为,确非池中之物。”蔡邕缓缓开口,声音带着长者的稳重,“冀州如今气象一新,非复旧观。他既有此诚意,又念及旧诺,为父看,此去或是你的一个好归宿。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