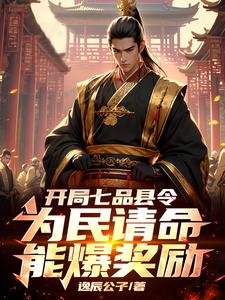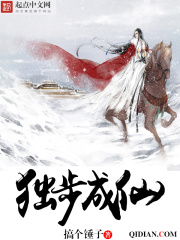第349章 压力如山
昨日均田司门前那场风波,并未随着贺舟的狼狈离去而平息,反而以一种更为诡谲的方式,在京城的上空继续发酵。
次日,五更天的梆子声刚刚敲过,天际尚是一片沉沉的黛色。一道寒风自宫墙高处掠过,吹得檐角下的宫灯摇曳不定。
御书房外,空旷的广场上,一个瘦削的身影直挺挺地跪在那里。
正是国子监致仕老祭酒,贺舟。
他换上了一身最为厚重的大儒朝服,满头白发在凛冽的寒风中散乱飞舞,那张布满皱纹的老脸冻得发紫,嘴唇干裂。
贺舟双手高高举着一面赤金令牌,正是先帝御赐的那面免死金牌。
他就这么跪着,不言不语,像一尊顽固的石像,用沉默对抗着皇权。
来往的内侍与禁军无不侧目,却又不敢靠近,只是远远地低声议论,目光中充满了敬畏与好奇。
三朝元老,士林领袖,手持先帝金牌,长跪宫门,这分量,足以让整个朝堂为之震动。
御书房内,暖炉中的银丝碳烧得正旺,将一室烘得温暖如春。
年轻的天子赵汝安却只觉得一股烦躁的火气从心底直冲头顶。
他将手中的朱笔重重掷在案上,溅起几点墨星。
“食古不化!顽固不灵!”他低声咒骂,眉宇间尽是无法掩饰的疲惫与不耐。
赵汝安起身在殿内来回踱步。
一旁侍立的大内总管梁宇,躬着身子,眼观鼻,鼻观心,仿佛一尊没有情绪的木雕。
直到赵汝安的脚步停在他面前,他才抬起头,用那特有的、不疾不徐的语调低声道:“陛下,贺老祭酒毕竟是三朝元老,在士林中声望极高。他这么跪着,怕是不到半日,京中便会传得人尽皆知。届时,恐怕于陛下的声名有损。”
赵汝安深吸一口气,胸中的怒火被强行压下。
他何尝不知这个道理。
贺舟这老匹夫,是在用自己一生的清誉,用天下读书人的悠悠之口,来逼他就范。
“罢了。”赵汝安坐回龙椅,脸上的烦躁瞬间被一层温和的面具所取代,声音也恢复了帝王应有的沉稳,“宣他进来吧。再给他赐座,上好茶。”
梁宇躬身领命,退了出去。
不多时,被寒风侵袭得几乎僵硬的贺舟,在两名小太监的搀扶下,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御书房。
暖气一扑,他浑身一颤,打了个哆嗦。
“老臣贺舟,叩见陛下!”他挣开太监,便要再次下跪。
“贺老不必多礼,快快请起。”赵汝安亲自走下御阶,虚扶了一把,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关切,“来人,给贺老看座,上热茶驱寒。”
贺舟被按在锦墩上,一杯滚烫的参茶递到手中,他却无心去喝,只是捧着,浑浊的老眼中便涌出了泪水,声音哽咽:“陛下啊!老臣今日是舍了这张老脸,也要为我大安的祖宗基业,向陛下进一言啊!”
他将昨日在均田司门前未竟的哭诉,添油加醋地又演了一遍,将余瑾清查田亩、调控粮价之举,描绘成了动摇国本、与民争利的苛政。
言辞之间,句句不离“祖宗之法”、“社稷安危”,仿佛余瑾已是祸国殃民的奸佞,大安王朝已在倾覆的边缘。
“恳请陛下,收回成命,罢黜余瑾,以安天下士人之心,以固我大安百年国祚啊!”说罢,他将茶盏往地上一放,便要再次离座叩首。
赵汝安始终面带微笑,静静地听着。他时不时地点头,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,眼神却深不见底,看不出喜怒。
“贺老的忠君爱国之心,朕明白了。”待贺舟哭诉完毕,赵汝安才温言安抚道,“此事干系重大,朕会审慎考量。贺老年事已高,切莫再如此折腾身子,快回府歇着吧。”
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,既表达了对老臣的尊重,又未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。
贺舟还想再说什么,却被赵汝安一个眼神制止,只得在梁宇的“护送”下,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御书房。
殿门合拢,隔绝了外面的天光。御书房内,赵汝安脸上的温和笑容瞬间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阴沉。
他走到书案旁,看着那堆积如山的、弹劾余瑾的奏章,只觉得一阵头痛欲裂。
夜色渐浓,华灯初上。
当京城的大部分角落都已归于沉寂,御书房内却依旧灯火通明,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。
赵汝安疲惫地揉着眉心,将最后一本奏折丢开。
“梁宇。”
“奴婢在。”
“秘密传余瑾入宫。”赵汝安的声音里,再也听不到白日里的沉稳,只剩下压抑不住的烦躁。
一道黑影自宫中悄然驰出,直奔平章事府。
余瑾被内侍引着,穿过幽深寂静的宫道,来到御书房前。
他心中早已了然,这一趟,必然是因贺舟而起。
踏入御书房,一股沉闷的压力扑面而来。
赵汝安并未坐在龙椅上,而是站在那堆积如山的奏章前,脸色在烛火的映照下,显得晦暗不明。
“参见陛下。”余瑾躬身行礼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