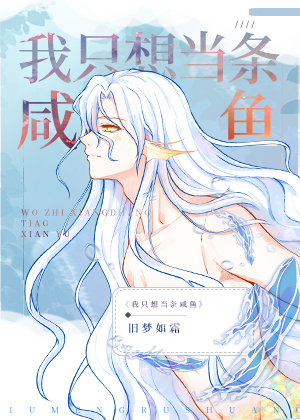宿缃的脑子被张仕安的话绕的混乱,一时不能给出任何反应。
“再说了,那些人怎么没吃的没喝的。”张仕安瞥了一眼宿缃,道“我日日给他们送去吃的,村外面不是有河有溪流嘛,他们怎么没有吃的喝的?”
宿缃挣扎着挺直腰板,盯着张仕安:“病死的人全部被丢到溪水里,那水怎么喝?”
“有什么可怕的?”张仕安剔着指甲里的陈灰,“反正迟早都要死的。”
“没错,反正迟早都要死的。”有泪水盈在宿缃眸子里,宿缃抬头,强忍着将泪水咽下。“疫病刚刚爆发之时,城内染病去世的人只有100人,然而,不到七日,染病去世的人就将近七千人。”
张仕安怔了怔,将翘起的脚放下,俯身看向宿缃“你想说什么?”
“你是怕了吗?”宿缃癫狂的大笑着“你怕我把你的秘密说出来吗?”
“我怕?”张仕安笑得疯癫“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怕?”
“有多少与你交恶的对手被你当做是病患撵出城?又有多少姑娘由于不想满足你的淫欲,全族都被你当做是病患撵出城?你有没有算过你欺上瞒下,将未发病的人当做是病患上报,一共冒领了多少赈济钱!”
张仕安向旁边的小递了个眼神。小厮会意,手一扬,身侧压着宿缃的两个人抬起右脚,把她踩在地上,十几个甲兵一拥而上,对她拳打脚踢。
“在男人身下混日子的臭婆娘,我给你点好脸你他妈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了是吧!”张仕安用脚踩着宿缃脸,啐道“还想着为那些贱种讨公道!”
“没错,我是把那些不听话的狗东西都弄出了城,我是故意让他们自生自灭,我是间接杀了那些贱狗。可你有什么立场说我。”张仕安使劲从宿缃手中拽出那把短刀,用刀剑自她的脸颊一路滑下,“你就是用这把刀杀了王家二百多口人的吧!”
“王家人该死。”宿缃道“王戍奕与你勾结,你们把那些交不起田赋的人全部当成病患撵出城,夺了他们的命,又夺了他们的地!”
“你和你父亲还真是一模一样啊,一样的愚蠢。你们不过都是我脚下的狗,怎么,还想着反过来咬主人一口?”张仕安捋了捋胡须,突然想到了什么,“哦,对了,你父亲的奴籍籍契还在我这呢!”
宿缃咬紧牙关,看向张仕安:“张仕安,你就不怕遭到报应吗?”
“报应,什么报应?”张仕安五指掐在宿缃的下巴上,狰狞地笑道“十年前的一切早已是死无对证,今日你也会死在我的手里。”
张仕安抬起手就向宿缃的喉咙刺去。然而,忽然间,君子意破风而入,张仕安握刀的那只手滚落在地。
宿缃抬眸一看,初颜、墨殇、司马聿清已带人将屋子围的水泄不通。
*****
宿缃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,刚开始还只是打打哆嗦,后来便全身不受控制的抽搐。医官忙着去煎药,外人都被司马聿清安排在门外,屋里只留下了初颜一人。
屋子有些冷,初颜拿过火盆,点了火。
“你不是害怕火吗?”宿缃眼睛半睁半闭,哑声道:“没事的,我不冷。”
初颜没回答,自顾自点了火,将火盆放到床边。她将椅子挪的离火盆远了些,用手蘸取了些药膏。
宿缃疲惫至极,似有千斤巨石压在眼皮上。
“先别睡。”初颜用拿着药瓶的那只手轻轻拍了拍宿缃的肩,轻声道“一会药就煮好了,你再挺一会,喝完药再睡。”
宿缃歪过头,睁开眼睛,看向初颜“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今夜要对张仕安下手的?”
“墨殇派人查了你的底细,知道十年前你的父亲死在张仕安的手中。你之所以跟我出府,就是想伺机报杀父之仇,仇人既在眼前,你怎会不动手?”初颜为宿缃轻轻涂着药 “我只是没想到王戍奕一家人也死于你手。”
“十年前,王戍奕还是涿城大地主,手下佃户一百五十一户,共五百一十二人。”宿缃眉头紧蹙,眸子盯着那黢黑的床顶。床顶似有什么在织了一张又密又大的网,宿缃的眼神似是被那网缠缚住了,她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开,反而越缠越紧。顿了半晌,宿缃闭上眼睛,“疫病爆发时,王戍奕将交不起租的四百六十三人上报为染了疫病的人,将他们全部扔进了疫区,而后强制收回了那些人手中的租田。被扔到疫区的人很快就都染上了疫病,不治身亡。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弟弟也都在住进疫区的第四日不治而亡。”
初颜抿着嘴,低头不语。该上药的地方都涂好了药,初颜将手中的药瓶放在桌上。
宿缃睁眼看向窗外“八年前,涿城大败后,民不聊生、国库空虚,而涿、棫州二城的商人却赚足了国难财。此二城虽无地可种,可朝廷下发的赈济粮确实大数目。以张仕安为首的地方大员勾结富商,私吞赈济粮,不顾百姓死活,谋取大量的财富。彼时,先皇为了填补国库空虚,从商人手中筹集更多金银、粮食,听从了冯文苳的建议,施行‘中盐’改革。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