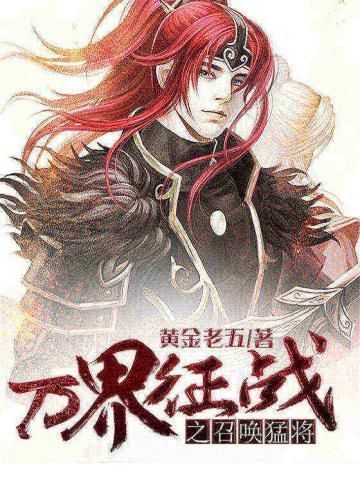第267章 皇子就了不起了?
他身边那些军官,带头涌上。
他们作为军官,已参与叛乱,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宽恕的。
门口那些军士,则盯着紫镇东手中令牌,犹豫不前。
冲皇子使命,他们知道那是什么罪,是会祸及家人的。
紫镇东另一只手抄出了刀,同时道:“你们现在退出门外,我便不记得你们是谁了。”
军士们茫然对视,而后缓缓往后退去。
刘梁目光一缩。
他的学生,确实很聪明。
聪明内敛,从不多言,长相可爱,却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最硬的事来。
在自己即将得势时,举刀而出,带头反对自己!
铿!
紫镇东已拔刀,冲向那些人。
陆轩也反应过来,立马道:“不要管我,去帮他!”
噗!
他话音刚落,紫镇东手起一刀,砍死一人。
鲜血淋漓,模糊在那张坚定的脸上。
他有些黏糊的声音再度响起:“奉六皇子命,接管张梓城,镇压叛逆!”
“小子,毛都没长齐,就想一力擎天!?”
一人大吼,抡刀劈来。
紫镇东侧身一躲,反手一刀攮进他胸口。
刀锋刺入瞬间,手腕一拧一拔,又一军官毙命于其刀下:“奉六皇子命,接管张梓城,镇压叛逆!”
他不断重复着,像是在坚定自己的心。
使的年少的他,杀气愈添。
步伐一往无前,刀锋愈挥愈快,喝声渐渐如雷。
随着躺在他脚下的人愈来愈多,那些旁观者也开始站了起来。
不知何时,刘梁身前的人已尽数伏罪。
紫镇东刀尖滴血,山壁上多出了几道垂死挣扎留下的刀痕。
还有碎裂的肉沫、血和着内脏与脑浆,粘附在那面巨盾上。
并不算高大的少年立在刘梁面前,巍峨的像是一座山。
在刘梁看来,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少年,藏锋多年,终如星辰破空而至,撞的却是他这个老师。
是他之幸,也是他之悲。
在陆轩等人看来,局势将倾,颓破在即,这少年犹如一面山壁,硬是擎住了这一角斜天。
还有那枚令牌——看来早在数日前,六皇子便和他商议过此事,且留下了后手。
陆轩无比庆幸,自己和秦度安排了这个少年去送信。
刘梁叹了一口气,道:“我知道你会有出息,没想到你会踏着老师的尸体来扬名。”
杀人之后,紫镇东无比坚定。
他抬起刀,指着刘梁:“因为你,不再是当年的你。”
“你背叛了国家,也背叛了当年的你!”
没有丝毫动摇,坚定的可怕。
“你要杀我吗?”刘梁握紧了刀:“弑师扬名,靠我的人头立功,你知道世人会如何说你吗?”
紫镇东没有废话,一刀劈了上去。
太快了,没有任何犹豫。
刘梁大骇!
他说那些,便是用言语攻势来影响少年心态。
对方毕竟年渺,感情牌一定有用……这是刘梁的想法。
他已经尽可能高估自己的弟子,但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。
以至于,刀尚未出鞘,人头已落地。
噗!
鲜红的血喷了出来,铺成一道残忍的红霞。
紫镇东转过身来,没有半点彷惶。
“他们会说我是英雄。”
少年如是道。
他将方才起身支持刘梁的人,全数杀光!
绝处逢生,陆轩等人喜出望外。
但问题,还是摆在他们面前:
粮食如何解决?
斩刘梁等人后,城中愈发浮动的人心,又当如何解决?
紫镇东决定将叛逆之人家财抄去,换来粮食,能多顶一日算一日。
在将刘梁等人头颅悬于城门后,布告全城:敢有叛国投敌者,当如此!
城中军事力量最强的刘梁都被宰了,可想张梓人在看到这些人头后,内心有多么震撼。
随后,他还耍了一个小心机:找了两拨军士,每隔一段时间在城楼上跑动,并且抛动火把——目的是为了吸引城外叛军主意。
果不其然,韩雄在城外硬等一个时辰后,见城门始终未开,不由焦躁:“莫非是缓兵之计?”
“如果是缓兵之计,他何须说一个时辰?”张英道出疑点。
刘梁完全可以说等明天再下手。
韩雄一愣,点头:“有理!”
不久,探子来报,说城楼上有异动,此前脚步阵阵,隐隐有厮杀声传来。
“确实是动手了!”韩雄大喜,又道:“只是刘梁能力泛泛,竟没能一口吃下陆轩,使局势焦灼了起来?”
“要不要趁机举兵攻城?”有人问。
“不妥!”韩雄摇头否定,道:“高层变动,底层尚不知,见外敌来攻,他们会本能联手抵抗,反而坏了刘梁的事……等!”
——子时,中。
腊月二十六。
在主力大军还在翻山前行,赶往天井关时,甄武、丁斐领八千骑兵赶到了天井关西侧的西河。
左中郎将褚飞闻讯从前方赶来,至深夜才临城,命西河营急摆酒为二将接风。
不同于并州东边的叛军主力猛扑进攻,西边主要以防备为主。
现在来了这么一支强军辅佐,褚飞当然高兴——自己败军的风险基本归零,等到趁势而进时,还能捞不少战功。
幸好有太尉来做总帅,有老领导带着就是爽!
想那秦度,要不是抱上了六皇子的大腿,凭什么一跃就成了自己顶头上司?
风水轮流转,如今到我了!
甄武是个直脾气,听褚飞大概描述后,立马不乐意:“既然西边战事不急,太尉让我们来此作甚?东边正缺人呢!”
“诶!甄将军且坐,不要急嘛!”
褚飞长得五大三粗,但却是个人精,端着酒杯,面带笑意的靠了过来:“西边虽局势稍缓,那是因为我们这和东边不同。”
“并州东边,汉人多而异族人少,西边则恰恰相反。”
“如今西原未动,所以那些小部落动手的也极少,多是在暗处浑水摸鱼。”
“可一旦局势再乱一些,西边压力必然陡增,西河又不如天井关险峻,届时如何防守?”
“朱公虑事在先,运筹帷幄,使我军先立不败之地,可称‘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’了!”
甄武面色一沉,正待反驳时,门外有人走了进来:“报将军,门外有人求见,说是六皇子所部,持令来见甄、丁二位将军。”
褚飞一愣。
甄武立马起身:“愣着干嘛?请他进来!”
不一会儿,一名甲士入内。
奇怪的是,他除了带着命令外,手里还提着一坛酒。
“曹汾!”
甄武一眼便认出了来人。
曹汾微微点头,掏出文书便道:“平难将军、督三河五校六营军事、六皇嗣彻令!”
三人连忙离席,单膝跪地:
“末将在!”
褚飞是太尉和周汉的人不假,但他的顶头上司,先是他的老搭档——镇原将军秦度。
秦度上面,是总督一府三河五校六营的周彻。
再往后,才是此番北讨的总帅太尉。
周彻的正式命令,他焉敢不尊?
“褚将军,念你镇守西部,甚是劳苦,听闻你酒量甚佳,特取御酒一坛赐你。”
“使者到时,请将军满饮此酒,以慰忠臣之意。”
“这……”褚飞愕然,一时迷茫。
六皇子这是什么意思,拉拢自己?
直接酒里下毒,给自己干了?
没必要啊……
“请吧,褚将军。”曹汾将酒送到他跟前。
“这……”褚飞找了个借口推辞:“局势紧张,哪敢痛饮?”
“定阳尚在,何况西河?”曹汾道:“何况是殿下之令,你只是奉命行事。”
“我酒量平平,喝不得这许多酒,只能浅尝。”褚飞又道。
“这可是殿下大婚之日,陛下所赐之酒,如此美意,您怎么能辞呢?”曹汾又道。
褚飞没有办法,更不知道周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这算什么军令?
稀里糊涂的干了两碗酒。
谁知这酒不是一般的烈,干完之后,他就稀里糊涂的趴在了桌子上。
哗!
这里都是褚飞的人,见自家将军倒了,一群武人立时起身。
“怎么?你们担心我会害了你家将军?”
曹汾眼睛一扫,哼了一声:“褚将军为国解忧,有功无过,殿下素来赏罚分明,为何要害他?”
“若是褚将军有罪,我便不是提酒来,而是请节杖来,将其斩首便是,何须玩这花招?!”
他将那坛酒提起,给自己也倒了小半碗,美美的喝了一口,又目光一扫:“你们放心,在褚将军醒来之前,我不会离开此处。”
“无论出什么事,都由我、由我身后的殿下担着,明白了吗!?”
既是六皇子特使,那在此便是代表六皇子,众人不敢怠慢,齐声应道:“我等知晓!”
“那就行。”
甄武眉头紧皱,凑过来问道:“这是做什么?”
“这是给两位将军的。”
曹汾收敛狂放姿态,将两封命令塞到二人手中。
丁斐正要拆开看,曹汾拦下了他:“回营再看!”
“好!”
两人一回营,便迫不及待将其打开,见令如下:
“你二部沿大新山脉向北,直插张梓城。按时间推算,须在腊月二十九卯时之前,抵达张梓城西边的麓谷地带。
顺利抵达之后,于山顶焚烟为号,待张梓城以狼烟响应,作如下安排:
考虑地形因素,骑兵在麓谷中央道路展开时不宜过多,否则易自相践踏。令甄武部五千骑下马改为步战,伏于麓谷;
丁斐部长水、越骑、屯骑三营,以长水骑为先锋,引诱进攻张梓城外叛军驻营,引敌骑来攻后,迅速折回麓谷;
屯骑不进入麓谷地带,沿上溪一路前行,绕至张梓城北。城北地形开阔利于骑兵冲锋,待张梓城城门大开、城中军队出击时,屯骑即刻发动,直捣敌人主阵;
越骑营居中策应,作为两处战场的预备队。
见信即刻行动,不得延误!”
对于周彻的命令,两人不敢有丝毫质疑,立即开拔。
城外营动,消息自然被褚飞的耳目探知。
他们想要告知褚飞,可褚飞又醉而不行,况且有曹汾在,甄武、丁斐两人也是执行上级命令,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?
直到次日大上午,褚飞吃力的睁开眼睛。
啪啪啪!
曹汾忍不住鼓掌:“传言不虚,褚将军果然好酒量。”
褚飞紧锁着眉头,用手扶着额头:“特使……”
“褚将军既已醒来,我的任务也已完成,就先告辞了。”
曹汾不和他废话,转身就走。
褚飞望着曹汾匆匆而去的背影,忍不住嘀咕道:“莫名其妙。”
“将军!”
这时,他的部下方来告知:“昨夜您醉酒后,甄丁二将军回营便举众开拔,沿大新山脉而下,往西北方向走了。”
“什么!?”
褚飞大吃一惊:“为何不早说!”
“您醉而不醒,他又守在这,我们没法说啊!”部下告苦。
吃惊之后,褚飞沉默了下来。
六皇子要调动大军,为何要让自己先醉酒?
有了!
他是要拖延自己的上报时间,以达到瞒过太尉的目的!
他并未向太尉屈服,采取防守的政策,而是坚持出击、救援张梓!
而且看曹汾到来的速度,只怕甄、丁二人动身不久,六皇子便安排他上路来追了!
“快!给我备快马,立即向太尉去信,就说甄、丁二将忤逆其令,率众绕行大新山脉,往西北方向去了!”
“是!”
快骑出西河的时间,大军才至天井关。
太尉朱龙召开紧急军议:“知我抵关,敌人必有备于南。”
“张梓中南地形,诸位可见,如此破碎,难容大骑作战,唯以步兵当先。”
“以步兵缓缓推进,多遣哨探,沿途排查伏兵,推行至张梓城下,才是稳妥之策。”
“若贸然急进,中其围点打援之术,将再遭秦度覆辙。”
他的言语稳重,众人难以反驳。
张梓情急,叛军也知道朝廷军急着来救。
一旦如其所愿,焉能不中套?
“殿下以为如……殿下呢?”
朱龙目光一扫,才发现周彻不在。
董然道:“殿下未曾与会。”
他背后董问几人,面露冷笑。
皇子就了不起了?
真以为凭河东之功,就能横视军中?
真到了大军中,还不是一个回合,被太尉收拾的服帖!
赵远图叹道:“殿下知秦将军负伤,抵关第一时间便去看他了。”
“体恤将士,这自是好事。”太尉点了点头,又道:“不过,秦度冒然进军,以至朝廷军败失士气,自身又带伤卧床,难当方面之任。”
“我意,暂撤秦度镇原将军一职,由原左中郎将褚飞领之。”
“此议甚妥。”董然点头:“可先让褚飞于西河领事,再差快马去见陛下,禀明此事。”
“嗯……”
朱龙点头,犹豫了一会儿:“先去和殿下商议一下吧!”
毕竟,秦度是周彻的人。
——屋内,秦度面色苍白:“臣有负殿下所托。”
秦度冒险驰援张梓城,除了大局外,还有就是自身立场。
他是并州六营总将,对并州的责任心强于其他人,是其一。
还有便是他是周彻的人,必须贯彻周彻的路线,这是他对周彻的义务。
“不需此言,你好好养伤,其他的交给我。”
周彻摇头,同时问道:“张梓城的情况,你知道多少?”
“很难守住了。”秦度叹气,道:“被一郡之守焚了粮仓,又多接纳了数万人,现在不破,已是难得。”
“军议我没去,但依太尉的意思,必是求问缓进。”周彻道:“此去张梓不远,问题是地形破碎,极容易伏兵,若是步兵缓行,非三日不可抵达。”
“我意亲往张梓,以定大局。”
“不可!”秦度连忙劝阻:“叛军众多,其他人都可以冒险,殿下您怎么能亲自担如此风险呢?但有万一,大局如何?”
“哪怕在并州吃下这个亏,日后我们不是没有机会!”
“你不必再劝,我有提前安排,此行不算冒险。”周彻摇头:“你只需告诉我,该怎么做,才能绕过太尉的视线。”
秦度叹了一口气,让人将舆图取来,以手指之:“在天井关东侧,有一条窄涧,名为埋羊涧,宽约丈余,可以走马,直通关外……”
因地形特殊,这里只需少数人把守,便能将来犯之众悉数活埋在其中。
看守在那的屯长,是秦度的人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周彻点头。
恰好这时,太尉来了。
他先向周彻行礼,又过问秦度伤势。
在说过几句场面话后,他叹息道:“秦将军初受重用,建功迫切,此心我能理解。”
“可你既担方面之任,怎能率轻骑突进,逞匹夫之勇呢?”
“如今身体有恙,卧床不起,何以担任,岂不是有负国家之托?”
“何况叛军一朝得势,聚众十余万,其势大如此,何以数百骑相争?”
“殿下,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?”
被这样的人物指责,秦度无力反驳。
“不是!”
但周彻可不会,立即道:“贼势几何,我未曾见。我只见血尚热者不愿辜负皇恩,历险尤愤、纵败不屈!”
“位尊禄厚将朽之人安享前勋,只知求稳,视生民于不顾!”
“口口声声为了天下大局!并州非天下之一么?并州遭劫之百姓、张梓城内那些生灵,便不是大局中人么?”
“太尉说骂名你一肩担之,届时若因你延战之故,并州死伤之众,你也能一并担之吗!?”
周彻的猝然爆发,使得屋内立时陷入了寂静之中。
前番交锋,似以太尉得胜而告终,竟让他们忘了这位皇子的脾气。
需知在出兵之前,他在雒京城亲自碾碎了一公一卿一皇子啊!
赵远图眼观鼻,沉默不语。
朱龙缓了过来,叹道:“看来殿下还是对我的求稳不认同,不如您上书陛下,只要陛下答应,老臣愿卸下这主帅之职,交付殿下。”
——你要么拿掉我这个主帅,你如果做不到,那在军中还是我说了算。
周彻讽笑:“太尉似乎不敢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周彻在说责任,而朱龙则在谈卸任。
“并州之祸,生灵受难,责任在韩问渠、在叛军。”董然道。
“责任也在害怕担责,惧而不战之人!”
说话的是随行的皇甫超逸。
他的军职不高,奈何人家靠山太大,除了周彻还有皇甫氏撑腰。
“秦度饮败,负伤难起,我意让褚飞暂领此职,殿下以为如何?”朱龙绕开了这个话题。
“我不同意。”周彻想都不想就回绝了:“负伤便要停职,将来哪个将领敢冒险?”
“我讲的是当前之势。”
“我讲的是日后之路!”
“叛军势如此,只能顾眼前。”
“叛军势如何?我怎未曾见!”
周彻豁然转身,盯着朱龙:“太尉,叛军势如何?”
“火焚六郡,残民百万,威胁三河,势已滔天。”朱龙回道:“我见得多了,深知败军只在骄兵之时,一旦失利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周彻笑了:“太尉,你老了。”
朱龙愣在当场。
周彻已转身离去。
董然蹙眉:“太尉,褚飞之事?”
“容后再商量。”朱龙摆了摆手。
周彻总督六营,这件事绕不开他。
等到离开此处,董然又道:“方才六皇子所言,似有归责于您的意思。”
朱龙笑了,道:“只这一条路走,如何证明我是错的呢?”
“陛下不问过程,只要结果……只要我最终能平定并州之乱,便有功无过,谁也究不了我的错。”
“何况,我有错吗?”
“自然无错!”董然失笑:“他太年轻了,且在河东刚立奇功,自是急切之时。”
“他的急切不是立奇功,而在于并州的主动。”朱龙轻轻摇头:“一步缓,则步步缓,他深知此理,却又无可奈何,故今日猝然爆发。”
“原来如此。”
随后,朱龙下令,命步卒率先入驻关内,骑兵驻于关南。
使团营内,梁乙甫询问身旁人:“他们备骑兵了吗?”
“没有,他们将骑兵放在军后,不打算动用。”随从回道。
骑兵步兵动静差距很大,是瞒不过同行军的人的。
梁乙甫微微点头,走向萧焉枝帐中——萧焉枝依旧被扣在周彻帐里,唯有她的婢女在此。
“我清楚。”
婢女点头,将信绑在海东青脚上:“夜黑之时,再行放出!”
周彻主帐内,皇甫韵道:“一定要当心,除了盖先生外……这十人你也带去。”
她将手一引,帐外走进十个雄壮大汉,尽是身材高大,面容凶悍粗犷之辈。
一眼便可看出,他们和汉人长相有所差异。
周彻目光微动:“湟中义从?”
湟中义从,是凉州精锐,主要由西凉一带的羌族和其他各族勇士组成。
他们听命于大夏,随军征讨。
“应该叫他们为斗安义从。”皇甫韵道:“湟中义从中,会择选勇士,力冠百人者,授斗安义从。”
周彻没有跟她客气,连带着十名斗安义从在内,共领百骑。
这百骑之中,除盖越、许破奴外,还有马修、叶镇山这样的老五送到河东的武人。
周彻择其中精锐可用者,得强悍武夫二十余人。
河东百万众中,力撼一方的勇士四十余人。
其余的,则是最开始追随周彻的甲士中,挑出了最善战的二十几人。
他在里面披上铁炼衣那件坚不可催的细甲,外面又裹上一层铠。
将九歌挂好,提起一口大槊,翻身上了一匹皇甫家从西凉送来的宝马。
引众百人,入埋羊涧,向北直行!
——张梓城
紫镇东斩刘梁后,硬是用疑兵之计演了韩雄一个晚上。
直到天快亮时,韩雄等人才察觉到不对。
“恐刘梁失手。”
就连对张梓城内了如指掌的张英都这般说:“张梓离太原颇有距离,卷入并州大案的人不多,有相当一部分人未必愿意造反。”
“如果秦升尚有余力,陆轩团结城内之人,或已将刘梁镇压。”
韩雄脸沉了下去:“极有可能!”
他安排人小心靠近城墙,打算先通一顿话。
“放!”
谁知,紫镇东早已候着,见人过来,立即下令。
军士起身,箭矢怼着脸射下来,将一片叛军掼倒。
韩雄大怒,下令攻城。
他将进攻部队三分,分别由吕轻山、薛定和张英率领。
每人负责四个时辰,十二个时辰轮番攻击,不给城中片刻喘息之机。
“一日之内,必破此城!”
从腊月二十六卯时初,到腊月二十七丑时,张梓城已接受十个小时的强攻。
知道城中刚刚经历了一场冲突,也知道城中早已粮尽的叛军,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进攻。
等到换班张英上时,韩雄征调所有可用兵力,用来破城。
最后四个时辰,他一定要踩碎这座城!
吕轻山年纪较大,终是稳妥人,道:“公子,天井关有大军在,是否要提防?”
“吕公勿虑!”韩雄成竹在胸:“天井关将骑兵压在关后,朱龙没有要奔驰来援的意思,现在正是集中力量破城的好时候!”
张梓城上,血气如烟,糜肉墙石。
紫镇东倒退了两步,碰的一声倚在墙垛上,缓缓坐了下去。
他身边的青年笑了一声,将水囊递了过来:“镇东,喝口水。”
“谢谢。”紫镇东接过,往嘴里一倒之后,却愣住了:“米汤?”
“放心,那种不要脸的事我可不会做。”青年呲牙笑了笑:“我进食的时候,留下了一半,混在水里,饿的实在顶不住就灌一口……”
说着,他伸手揉了揉肚子,掀起外甲,将那根袋子系得更紧了一些。
“叛军一直来袭,能上场的弟兄又不多了,就吃这么点东西,确实顶不住啊。”
他叹仰面看着天空,想要抬手,但为了节省力气,又垂下了:“镇东,可真有你的,竟然能一刀宰了刘梁,稳住城中大局。”
“可是……不是哥说话不吉利,我们怕是支撑不到天亮了。”
阵亡者、伤员、叛逃者、畏惧藏匿者、因饥饿失去战斗力者……张梓城楼上,能防守的军士,已不足两千人。
而且多数饥饿、疲乏、伤势交加。
这就是战争的残酷。
一万人丢在场上,不是说打到一万人悉没才算输。
断粮、内斗、兵乱随便碰上一个,便是土崩瓦解,成片的战斗力丢失。、
“张六哥。”
稚嫩的人挑起了本不属于他的重担,有些茫然的提出了一个问题:“你说,我现在带人去强行借那些大户的粮,可行吗?”
“嗤——”
叫张六的曲侯笑了,道:“镇东,你想啥呢?你城守住了,人家是当富户;你城破了,人家照样当富户。”
“可你要是不让他当富户了,甚至纵兵抢杀他家,你说他会不会跟你急眼呢?”
“就算你杀尽了东家,那西家呢?”
砰!
城墙那头,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。
陆轩一脚印在石板上,身体晃了晃,险些栽下去。
他是此城之中,最早断粮的人。
使的原本就瘦弱的他,像是一块木板。
秦升也已断粮,加上伤势在身,已彻底陷入昏迷状态。
城楼上倚墙而坐的军士们,纷纷看了过去,眼中的光再颤抖。
充满了希望,但又知道希望的奢侈。
这些目光,使陆轩惭愧,他吃力的挥了挥手。
身后几人提着木桶上来了,开始分饭食。
说是饭食,其实主要还是水,里面混杂着极少数的麦麸、米粒和不知什么菜。
值得庆幸的是,里面还有一丝咸味,看来陆公用什么法子搞到了一些盐。
眼中的光再次破碎后,他们一仰头,将所谓饭食‘喝’了个干净。
而后继续躺着,节约能量。
多数人的身体在哆嗦,这是饥饿之后的自然反应。
张六哥晃了晃他的碗,虚弱笑道:“好像还没有我的‘米汤’浓。”
他从腰间拔出一口小刀,在背后的城墙上轻轻刮了起来。
唰唰响声中,墙石中落下一些灰,被他用手揉起,洒入碗里,搅了搅。
“张六哥!”紫镇东心一紧。
“不懂了是吗?”张六哥嘿嘿一笑:“铸这城墙的时候,添了糯米汁和白面土,这两样东西香着呢……你说那些大人物也聪明,早在当年就替咱们想好了今天,可真是好人啊!”
他端起碗,就要一口干掉,却被紫镇东抓住。
接着,黑暗中香味靠近。
张六哥手一哆嗦,抓住了:“这……这是什么?你小子藏私?”
“不是,是我此前见六皇子的时候,他送我的。”紫镇东道:“叫鸡蛋灌饼,你吃吧。”
张六哥深吸了一口气,问道:“你还有几块?”
“最后一块了。”
“我不吃了!我讨厌鸡蛋!”张六哥直接给他推了回去。
“张六……”
咚咚咚!
鼓声突然敲了起来。
张六哥连忙爬起:“你小子是个有出息的人,你不应该死在这!我活不了多久,给我吃也是浪费!”
说完,提着他的枪向前奔去。
紫镇东也顾不得再多言,只能大吼:“迎敌!迎敌!”
城楼上军士陆续爬起,都往前涌去。
石头、箭矢,早已消耗干净了。
这也是壮丁没法再投入战斗的重要原因。
守城,只能靠短兵相接、以命换命。
仗打到现在,还往前冲的人,早已经麻木了。
战死吗?
那就死吧!
如果朝廷大军能打回来,如果还能在自己腐烂的尸体中找到名牒,还能给家人换一笔抚恤金呢。
紫镇东的铁胆也早已耗尽,他抡着刀疯狂劈砍,堵住了右侧的敌人。
轰隆!
左侧传来一声巨响,那边的墙垛竟塌下去一片。
立在上面的叛军跟着摔了下去,拥在下方的叛军则被当场砸死。
可这对于守军而言不是好事,失去城垛后,攀城的难度变得更低了。
接下来的叛军一次性能登上更多,大大扩充了交战面积——形势变得更加危急!
时间推移,城墙上的守城军愈来愈少。
寅时,紫镇东暂时退回。
愈到这时,他愈得保持自己的体力。
“啊……镇东!”
一声大叫,一道人影从交战处挣脱出来。
他浑身血红,鲜血从头顶而下,泼满了甲衣,根本辨认不出是谁。
右臂也已残缺,砍得只胳膊上部。
他向紫镇东踉跄数步,血气缭绕,身上红点乱泼,溅在少年身上。
“张六哥!”
紫镇东大恸,连忙来扶。
“我活不下去了……别管我……你的饼呢?给我来一口,我们山东人最喜欢吃饼了……哈哈”
他大声笑着,悲怆中带着洒脱。
紫镇东赶紧取出,递给了他。
张六哥猛地咬了一口,囫囵咽下后,抛还给紫镇东:“饱了!记得,我斩首十一颗……我妻早死,还有老母和幼子在家……”
“你小子要是活……活了下去,可不要……不要贪我的抚恤!”
就在这时,他身旁爬起一名叛军,一刀砍在了他脖肩位置。
“张六哥!”
“啊!”
张六哥嘶声痛吼,浴血的头颅猛地转了过来,盯着那人。
或许是那口饼真的让他‘饱’了,他奋力一跃,扑向那人,一同往城楼下跌去。
“第十二个!”
砰!
“张六哥!”
紫镇东悲声痛呼,抡刀向前,再度疯狂劈砍起来。
砰!
尸体落地,却是引起了督战的张英注意。
他看见了,一个接一个军士赴死而战。
他很清楚,这些人的血性已被彻底激发,他们在求死而战。
如此,此城虽能咬下,但要自己在规定的时间能攻破……须知道,自己新投晋王,这第一件事可不能办砸了。
这般想着,他眼中寒光一闪,朝着前方指道:“去,给我拖一具尸体来。”
下人不解,但还是照办了。
很快,一具满身是血的尸体被拽到他面前。
“撬开他胸前的甲片。”
下属照做。
“割开他的衣服。”
“那有个贴身的名牒,取下来。”
名牒很小,不到半个巴掌大,四面用针线固定。
上面留着的文字,是军士的籍贯、年龄、名字。
战死之后,朝廷会根据名牒发放抚恤,这是保证大夏军士死战的根本——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。
很快,张英得到了一把,他用火点燃,但没有让人完全烧干净。
随即,将残缺到无法辨认的名牒,重新抛上城楼。
啪!
啪啪!
一堆接着一堆被抛了上来。
而后是张英让人传出的喊话:“城破之后,名牒尽毁,你们死在此也是无名之辈!”
城楼上,悲狂的吼声有所熄落。
有军士茫然低头,突然迷失了。
他死志已存,一心求死而战,猝闻此讯,不知该退还是该进。
有叛军不断从墙垛后爬起,冲着发呆的守军便是一刀!
城楼上的抵抗力,遭遇重挫!
时间流逝,守军愈来愈少,叛军愈推愈进。
少年在癫狂之后,却镇定了下来。
他的眼神像嗜血的狼,没有了悲、没有了痛,唯有坚定的战意。
他没有用言语去号召同袍,而是不断战斗、厮杀、不屈!
饼未尽……
城未失……
我尚战,
你,会来吗?
横起一刀,将一人割下城去。
少年的眼神在前方无穷的黑暗中扫过。
黑压压的,那是叛军的大营,一眼看不到头。
轰!
忽然,这无边无际的黑中,一缕火苗蹿了出来。
被夜风一吹,那缕火在黑暗中乱滚,眨眼间撕裂开来,像四面扑去。
他来了!
周彻以百骑潜行,躲过了韩雄的耳目,并根据对方营盘布置选中一处,纵火径冲。
夜袭给敌人的最大伤害,不是手中的刀枪,而是混乱。
纵火,可以让混乱扩大。
叛军纪律极差,在夜里突遭火袭后,更是乱成一片。
周彻纵马率领百骑,在营中往来奔驰,杀进穿出。
“哈哈哈!”
知道破城在即,韩雄并未去休息。
在得知张英的打法后,他不禁大笑起来:“果然要知己知彼啊!早就应该让张公上了!”
“做得好!我原本以为他是个文官,未曾想竟有这般能耐,我得上奏父王,重用张公!”
轰!
突然,营后传来了动静,有人狂奔而来,慌张急促:“大事不好了!”
“能有什么大事?!”韩雄怒声呵斥!
“不知从哪冒出来一批人,突然冲入我军大营,纵起火来!”
“你说什么!?”韩雄瞬间失色,骇然问道:“是什么人?有多少人?”
“不清楚是何方人马,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。”
“混账!哨探呢?”
“明哨没有察觉到他们,有几处暗哨熄了,我们正打算派人去查探,结果对方便已点火……”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biqu09.cc。笔趣阁手机版:https://m.biqu09.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