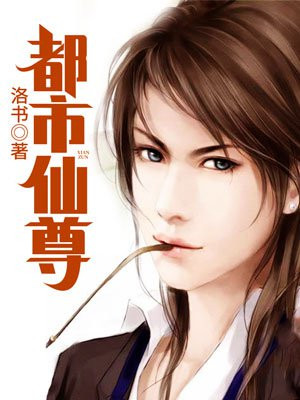第355章 单骑赴约惊鸿影,一局暗藏龙虎机
吴天翊一路往城南而去,马蹄踏碎残冬的冷寂,听竹亭终于撞入眼帘。
周遭竹林褪尽绿意,枯黄叶片在寒风中簌簌发抖,断枝坠向薄雪覆盖的地面,闷响被风揉得细碎。
吴天翊勒住缰绳时,“踏雪” 的蹄子已在冻土上凿出深浅蹄印,呼出的白气撞上凛冽寒风,瞬间凝成白雾又被撕碎。
他翻身下马,指尖触到袖中弩箭的刹那,竟觉那金属凉意比周遭寒气更刺骨 —— 衣下甲片硌出的褶皱,恰似他此刻绷得发紧的神经。
亭顶积着层薄雪,檐角冰棱在残阳下泛着冷光,将青石板亭面映得青白如霜。
石桌旁坐着的人裹在玄色貂裘里,领口银线绣纹在暮色中若隐若现,像是寒星坠落在墨色天幕。
她银发如瀑垂落肩背,鬓角几缕被风拂起,与貂裘边缘的白狐毛缠在一处,倒分不清哪是雪哪是发。
那人抬手执起竹制茶筅时,露出的手腕皓白如玉,指节却透着常年用力的薄茧,在铜鐎斗映出的火光里忽明忽暗。
她面前的陶炉燃着松柴,火焰舔舐着鐎斗底部,将那只三足器烧得泛出暗红,滚热的水汽从鐎斗细长的壶嘴涌出,带着草木的清气漫开,在亭内凝成淡雾,倒让这冰封天地里生出片小小的暖区。
身后侍立的丫鬟裹着灰鼠皮袄,垂手捧着紫檀茶盘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,腕骨处隐约可见凸起的筋络 —— 那看似恭顺的姿态里,藏着与寒冬相契的冷硬,仿佛随时能化作出鞘利刃。
亭外风卷雪沫掠过檐角,冰棱偶尔坠落,碎裂声与壶中茶汤的沸腾声缠在一处,竟生出几分沁人的安宁。
吴天翊眼角余光扫过石桌下的雪地,几处被刻意踩实的痕迹平平整整,像是有人细心拂过新雪,只留下淡淡的足印,与周遭的皑皑一片融成浑然的素白,瞧不出半分异样。
亭内的暖雾裹着茶香漫到亭边,与檐下的冷气相触,凝成细碎的冰晶,落在青石板上,倒像是谁撒了把碎玉。
连风穿竹林的声响都变得轻柔,枯黄的竹叶打着旋儿飘落,盖在新雪上,添了层浅浅的黄,倒比平日里更显静谧。
他缓步走入亭中,靴底碾过冻雪的咯吱声刺破茶香,那人抬眼时,眸光在他身上轻轻一落,清冽如溪涧融雪,却又藏着深潭般的沉邃,仿佛能看穿他衣下藏着的甲胄与心事。
“世子爷来得正好,” 她执起茶针在茶饼上轻旋,褐色茶屑簌簌落入锡罐,“再晚一步,这茶就要凉透了!”
声音像是被炭火烤过的温玉,裹着暖意却又带着玉石的清寒,“老身备了炭火,先暖暖手?”
风穿竹林时卷来枯枝断裂的脆响,那人垂眸倒茶的动作未停,茶盏边缘凝着的水珠已冻成细冰,在她指尖轻转时发出细碎的碰撞声。
吴天翊垂眸看向茶盏里的倒影,那少年被寒风冻得鼻尖微红,睫毛上甚至凝着细碎的冰碴,眼底的锐利却沉如封冻的深潭,不见半分十六岁年纪该有的波动。
仿佛北境的风雪早已将少年人的跳脱磨成了坚冰,只剩下历经杀伐后的不动声色。
他一言不发,转身在对面案几前跪坐时,锦袍下摆扫过地面积雪,只发出极轻的窸窣声,膝头触到冰凉石面的瞬间,脊背依旧挺得笔直,不见半分瑟缩。
并未急着回应,只抬手取过丫鬟刚添的茶汤,指尖捏住盏沿时,恰好避开了滚烫的部位 —— 那动作熟练得不像个养尊处优的世子,倒像早已习惯了在冷热交替中拿捏分寸。
茶盏在掌中轻轻转了半圈,热气顺着指缝漫上他的下颌,却没熏动他紧抿的唇角。
直到茶汤的温度透过瓷盏传到掌心,他才抬眼看向石桌对面的人,目光平静得像在审视沙盘上的战局:“您就是墨夫人?”
话音不高,尾音甚至带着被寒风冻过的微哑,却字字落得清晰。
问完这句,他便垂眸浅啜了一口茶,滚烫的茶汤滑过喉咙时,喉结只微动了一下,连眉峰都未曾蹙起 —— 仿佛此刻饮下的不是热茶,而是他早已在心中盘算过千百遍的棋局。
亭外风雪忽然紧了些,卷着枯枝撞在亭柱上发出闷响,他握着茶盏的手指却未晃半分,目光甚至还在茶沫消散的纹路里停留了片刻,仿佛那细碎的涟漪里,都藏着值得细究的机锋。
此时就见石桌对面的人望着他这副模样,执壶的手微微一顿,壶嘴悬在半空,滚热的水汽模糊了她眼底掠过的讶异。
她见过太多少年得志的权贵子弟,或骄纵张扬如开屏的孔雀,或故作老成似偷穿大人衣裳的孩童,却从未见过这般年纪,便能将沉稳刻进骨血里的。
更让她心头微动的是,这少年竟真敢应下这荒郊密会,不带一兵一卒,单刀赴会而来 —— 这份胆识,便是许多浸淫江湖多年的汉子都未必具备。
寻常人遇此境况,便是强作镇定,指尖也难免泄露心绪,可这少年握着茶盏的手稳如磐石,连睫毛上的冰碴融化成水珠,顺着脸颊滑落时,他都未曾抬手擦拭 —— 仿佛外界的一切动静,都入不了他眼底那方深潭。
这般年纪便有如此魄力,既敢孤身涉险,又能沉得住气,倒让她暗暗佩服起他这份临危不乱的定力与孤注一掷的决绝来!
再抬眼细看,才发觉这少年生得是真俊。眉峰如刀削般利落,眼窝深邃,鼻梁高挺,连唇线都像精心勾勒过的一般,偏偏组合在一起,不见半分脂粉气,反倒因那份沉静,添了几分惊心动魄的英气。
风雪落在他发间眉梢,竟像为这幅俊朗面容镶了道银边,难怪…… 难怪自己那三个眼高于顶的徒弟,会对他这般上心。
这般定力与风姿,倒让她想起那位淮南王世子来。
同样是藩王世子,那位吴瑾年偏生少了这份沉潜!
听说在京中权贵间周旋时,稍不如意便会沉下脸,被人三言两语撩拨便要动怒,眼底的嫉妒与浮躁藏都藏不住。
论起身份,两人皆是藩王嫡脉,论起境遇,都在这邵明城里步步为营。
可一个如风中残烛,一点火星便能燎起满腔怒火!一个却似寒潭冻玉,任风雪敲打,自岿然不动!
她收回目光,将第二盏茶推到他面前,茶汤在盏中晃出细碎的圈:“老身便是墨夫人!”
语气里添了几分不易察觉的郑重,“吴世子倒是比传闻中,更让人意外!”
吴天翊这才抬眼,指尖在茶盏边缘轻轻一叩,未接话,只将目光投向亭外风雪深处,仿佛在掂量她这句话里,藏着几分试探,几分真心。
风雪卷着枯枝撞在亭柱上,发出第三声闷响时,他终于开口,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:“墨夫人的信里说,张承宗邀了江湖好手,”
他头没抬,目光仍落在茶盏里袅袅升起的热气上,语气随意得像是在问今晨的雪下了几寸,尾音在茶香里轻轻漾开:“却没说,这些人究竟是哪路势力!”
那姿态里没有半分探究的急切,反倒带着种理所当然的从容,仿佛墨夫人在信里漏了这茬,本就是件该被随口点出来的小事。
亭外风雪恰好卷过檐角,冰棱坠落的脆响与他的话音叠在一处,竟让这看似寻常的问话,透出几分不动声色的压力。
“江湖势力,本就如野草般聚散!” 墨夫人将茶汤注入盏中,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寻常景致,“世子只需知道,这些人收了银子,便会按吩咐办事 —— 就像老身今日约你在此,也不过是想看看,燕藩的世子,究竟有几分斤两!”
吴天翊这才抬眼,指尖在茶盏底轻轻一旋,将沉淀的茶渣晃得浮起:“斤两?夫人是想称称燕藩的铁骑,还是北境的冻土?”
“自然是称称世子心里的秤!” 墨夫人迎上他的目光,银发在火光里泛着冷光,“老身听说,世子单骑入羌时,曾对羌族首领说‘北境的雪,埋过蛮族的骨,也容得下羌人的帐’—— 这话若是真心,燕藩便不该只守着北境的关隘。”
“夫人觉得,燕藩该南下?” 吴天翊忽然笑了,笑意却未达眼底,“像某些别有用心之人那样,在邵明城里养着私兵,盯着宫里的龙椅?”
“世子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。” 墨夫人执壶的手悬在半空,沸水在壶中轻轻翻腾,“大乾的藩王,哪个不是‘守境’的幌子下藏着野心?”
“可燕藩偏生不同 —— 打退蛮族不求封爵,收服西羌不掠土地,倒像只埋头拉车的牛,偏生这车上的人,还总想着卸你的轭!”
她话锋陡然转厉:“就说太后与徐阁老,一个想把你捆在后宫的绳上,一个想借你的铁骑稳固文臣的势,世子夹在中间,是打算做谁的刀?”
吴天翊垂眸浅啜一口茶,滚烫的茶汤滑过喉咙,竟没烫出半分波澜:“刀有刀的用处,但若持刀人想砍自己人,这刀便该钝了。”
他望向亭外被风雪压弯的竹枝,“燕藩的刀,只砍来犯的敌,不斩同袍的颈。至于旁人想借刀杀人 —— 得看本王肯不肯递这刀柄!”
“那世子觉得,如今这刀柄,该递向谁?” 墨夫人追问,目光如探灯般扫过他的脸,“是借徐阁老的笔,参倒你口中的那些人?还是凭太后的旨,压下文臣的势?”
“夫人见过北境的牧民放马吗?” 吴天翊忽然转了话锋,语气里添了几分漫不经心,“马群太野,便得用缰绳勒!可勒得太紧,马会惊!”
“如今的大乾,就像匹受惊的马,有人想拽紧缰绳,有人想抽鞭子,本王偏想给它喂口草料!”
“草料?” 墨夫人挑眉,“世子是说联姻?还是北境的铁骑?”
“都是,也都不是!” 吴天翊指尖在石桌上轻轻点着,“联姻是让邵明城的人知道,燕藩不想树敌!”
“北境铁骑入援京畿,是让天下人明白,燕藩守的是大乾,不是某个人的江山!至于那些想趁乱偷马的……” 他抬眼时,眼底闪过一丝寒芒,“便用马蹄子教教他们,什么叫规矩!”
亭外的风雪不知何时小了,只余细碎的雪沫在风中打着旋。墨夫人望着他平静的侧脸,忽然明白这少年的 “秤” 究竟是什么 —— 不是权欲,不是野心,而是一种更沉的东西,像北境的冻土,看似冰冷,底下却藏着能让草木生根的韧劲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