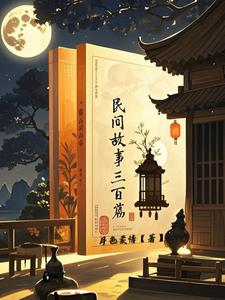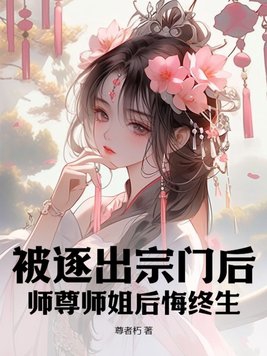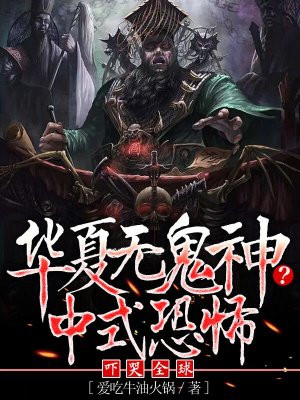这一年,林如海的独女林黛玉,年方六岁,因母亲贾敏病逝,外祖母念及外孙女无人依傍教育,便遣人来接黛玉去金陵贾府生活。
黛玉登舟起程,一路江水悠悠,心中满是对未知的惶恐。她自小身体孱弱,却聪慧过人,眉眼间透着一股灵秀之气。到了贾府,只见那宁荣二府,巍峨壮丽,雕梁画栋,往来的奴仆皆是衣着不凡。
进了府中,先是拜见了外祖母史太君,贾母一把将她搂入怀中,心肝儿肉地叫着,声泪俱下。黛玉也不禁落下泪来。随后,邢夫人、王夫人、李纨等一一相见。
正说着话,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,说:“我来迟了,不曾迎接远客!”黛玉心中正疑惑着:“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,恭肃严整如此,这来者系谁,这样放诞无礼?” 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。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,彩绣辉煌,恍若神妃仙子。这便是琏二嫂子王熙凤,人称凤辣子。
见过众人后,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黛玉去见两个舅舅。到了贾赦处,贾赦因说不忍相见勾起伤心,传话让黛玉好生休养。又去贾政处,王夫人告知贾政今日斋戒去了,叮嘱黛玉不要亲近那衔玉而生的宝玉,说他是个“混世魔王”。
正说着,外面一阵脚步响,丫鬟进来笑道:“宝玉来了!”黛玉心中正疑惑着:“这个宝玉,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,懵懂顽童?” 及至进来,却是位年轻公子:面若中秋之月,色如春晓之花,鬓若刀裁,眉如墨画,面如桃瓣,目若秋波。虽怒时而若笑,即瞋视而有情。
宝玉见了黛玉,便笑道: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贾母笑道:“可又是胡说,你又何曾见过他?”宝玉笑道:“虽然未曾见过他,然我看着面善,心里就算是旧相识,今日只作远别重逢,亦未为不可。”贾母笑道:“更好,更好,若如此,更相和睦了。”
宝玉走近黛玉身边坐下,又细细打量一番,因问:“妹妹可曾读书?”黛玉道:“不曾读,只上了一年学,些须认得几个字。”宝玉又道:“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?”黛玉便说了名。宝玉又问表字。黛玉道:“无字。”宝玉笑道:“我送妹妹一妙字,莫若‘颦颦’二字极妙。”探春便问何出。宝玉道:“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上说:‘西方有石名黛,可代画眉之墨。’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,用取这两个字,岂不两妙!”探春笑道:“只恐又是你的杜撰。”宝玉笑道:“除《四书》外,杜撰的太多,偏只我是杜撰不成?”又问黛玉:“可有玉没有?”众人不解其语,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,故问我有也无,因答道:“我没有那个。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,岂能人人有的。”
宝玉听了,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,摘下那玉,就狠命摔去,骂道:“什么罕物,连人之高低不择,还说‘通灵’不‘通灵’呢!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!”吓得众人一拥争去拾玉。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:“孽障!你生气,要打骂人容易,何苦摔那命根子!”宝玉满面泪痕泣道:“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,单我有,我说没趣;如今来了这们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,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。”贾母忙哄他道:“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,因你姑妈去世时,舍不得你妹妹,无法处,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了:一则全殉葬之礼,尽你妹妹之孝心;二则你姑妈之灵,亦可权作见了女儿之意。因此他只说没有这个,不便自己夸张之意。你如今怎比得他?还不好生慎重带上,仔细你娘知道了。”说着,便向丫鬟手中接来,亲与他带上。宝玉听如此说,想一想大有情理,也就不生别论了。
自此,黛玉便在贾府住下,与宝玉一处随着贾母起居,两人同起同坐,同止同息,亲密友爱日甚一日。
共读西厢
春光明媚,桃花灼灼,落英缤纷。一日,宝玉在沁芳闸桥边的桃花树下,正偷读那禁书《西厢记》,读得如痴如醉,全然沉浸在那才子佳人的浪漫情致之中。
正看到妙处,一阵风起,吹落了满树的桃花,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在宝玉的肩头、书页之上。宝玉正心疼着这花儿被践踏,想要将花瓣抖落河中,却不想黛玉担着花锄,挂着花囊,拿着扫帚,款步走来。
黛玉见宝玉手中拿着一本书,便笑着问:“你又在看什么书?”宝玉先是一惊,忙将书藏在身后,支支吾吾地说:“不过是些《中庸》《大学》之类的。”黛玉才不信他,走上前去,非要瞧个究竟。宝玉拗不过,只好将书递给黛玉,嘱咐道:“好妹妹,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,这可是禁书。”
黛玉接过书,只见封面上写着《会真记》三个字,翻开一看,里面的词句典雅优美,写的正是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。黛玉越看越入迷,脸颊渐渐泛起红晕,眼中满是陶醉之色。
待她看完,宝玉笑着问:“妹妹,你觉得这书如何?”黛玉轻轻地点了点头,赞道:“果然有趣,词句精妙,只是……”她微微顿了顿,眼中闪过一丝羞涩,“只是有些言语太过露骨。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