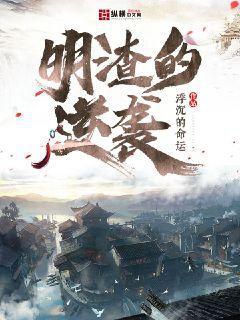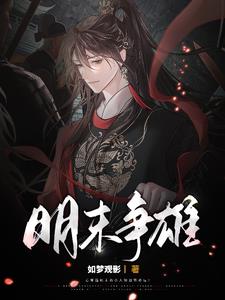自义军进入南京城,仅仅两个月,南京像是变了个模样。不仅破损的城墙基本修葺完毕,就连城内外坑坑洼洼的街道主官道也被修整,甚至道路两侧也多出了公共厕所,江面上巡弋的战船,城头上肃立执守的卫士,秋毫无犯,带给南京士民安全感的同时,城市变化日新月异。
几乎是很短的时间,江南总督府就已经收获了南京百姓,甚至江南百姓的民心。
对于那些久居于南京城的士民来说,南京归汉,已是欢欣鼓舞,而对于那些明末遗民,以及飘零海外者,就更是梦中惊魂,夜夜难熬了。
剑外忽传收蓟北,初闻涕泪满衣裳。
还没有登岸,只是看到仪凤门城墙上那高高飘扬的大明旗帜,年轻的朱毓仁热泪盈眶,就在那船头跪了下来,他头抵木板,身子不停抖动,涕不成声。
“天佑大明、天佑华夏……”
船头上的乘客,无不是心头沉重,有人摇头叹息,有人抹泪,有人神情凄凄。
梦里不知身是客,一晌贪欢。
独自莫凭栏,无限江山。
乘客中,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轻轻摇了摇头,他示意了一下,身旁的中年汉子上前,把朱毓仁扶了起来。
“先生,在下情不自禁,让你与世叔见笑了。”
朱毓仁擦了擦眼泪,朝老者与中年汉子行礼。
“贤侄,你这一路上,可是掉了不少的眼泪啊!”
中年汉子黄百家拍了拍朱毓仁的肩膀,笑道。
“远渡重洋,重归故土,再见大明旌旗,心有戚戚,人之常情,人之常情。”
黄百家的父亲黄宗羲,温声道。
朱毓仁,余姚人,久居日本,刚刚渡海归来,听闻义军破了南京,便邀同乡黄宗羲一同北上。
朱毓仁年纪轻轻,没有什么名头,但他的祖父朱之瑜,抗清义士,江南名士,先是追随鲁王朱以海,后又跟随国姓爷郑成功、张煌言北伐;期间三赴安南、五渡日本,奔走于厦门、舟山之间,向日本乞师复仇。
永历十三年,在看到清廷政权日趋坚固,复明无望后,朱之瑜流亡日本,被德川幕府破例允准定居长崎,学问与德行得日本朝野人士礼遇和尊重,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聘请他到江户讲学,许多学者都慕名来就学。
朱之瑜寄寓日本十多年,仍着明朝衣冠,追念故国,与黄宗羲交情匪浅。
“父亲,想不到王和垚这家伙,真打下了南京!”
黄百家看着越来越近的南京城墙,心情复杂,感慨地一句。
国姓爷郑成功当年北伐,数万锐士,还不是在固若金汤的南京城下铩羽而归。
这个朱和垚,他怎么就做到了?
黄宗羲点点头,看着南京城,心神不定。
何止是南京城,从浙江一路北上,苏州、常州、镇江等,以及江南府县,如今都已是浙江义军的天下了。
“世叔,你错了!皇孙不是王和垚,而是朱和垚,大明皇室的后人,崇祯帝的嫡孙!”
朱毓仁情绪恢复了过来,兴奋一句。
朱和垚,崇祯帝的嫡孙,可比弘光帝、隆武帝、永历帝等根正苗红的多。
至于什么周王吴三桂,就更是不值一提了。
“父亲,他……他真的是大明皇室吗?”
黄百谷跟着父亲上岸,仍是不能相信。
王和垚要真是朱和垚,崇祯帝嫡孙,他辱骂过,甚至是与皇孙动过手,岂不是把皇孙得罪透了?
幸亏父亲对朱和垚宽容忍让,又暗自资助了两万两银子。还有自己的叔父黄宗炎是浙江布政使,堂弟黄百谷还在武备学堂就读,都是朱和垚麾下。
希望朱和垚顾念父亲与黄家人的情义,不会难为他。
“我仔细斟酌过,应是皇孙无疑。”
黄宗羲点点头:“能以和垚为名,天下应是罕有。况且……”
黄宗羲顿了顿,这才道:“以总督大人今日之兵威,即便他不是皇孙,争霸天下,也不是没有可能,他又何必狐假虎威?”
也不知道,见了面以后,还能不能以“安之”称呼?
“父亲,朱和垚麾下不过万余兵马,又有什么兵威?万一清军来犯,他拿什么应敌?父亲此番北上,还是有些仓促了。”
黄百谷摇头道。
朱和垚虽然破了镇江南京等城,但人马太少。清军丢了江南,必然大军来攻,到时恐怕玉石俱焚。
父亲,还是太急了些。
“当年国姓爷北伐南京,五万大军,更有五千铁人军,非但未能攻下南京城,反而损兵折将,无功而返回台湾。”
黄宗羲道:“你看看总督麾下,攻下镇江南京不说,大破南京两万清军。义军如此兵强马壮,难道还不是天下强军吗?清军想要破了南京城,得多少兵马?你想过吗?”
“不错!梨洲先生所言极是!”
朱毓仁连连点头,目露喜色。
“我等一路北上,沿途所见,那些水师将士都是虎贲猛士,如此精锐,配以火器凶猛,清军绝不是对手!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