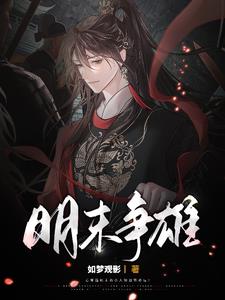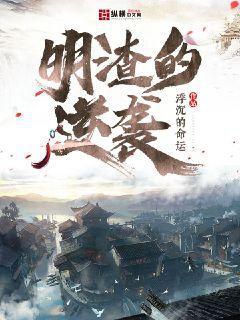离经叛道、中华非华。
南京城内外,总督衙门大兴土木,除了修葺城墙道路、建造厂房等,学堂的兴建也是当前南京城的重点,其中南京大学堂的改建与招生,似乎在预示着,总督府想要江南长治久安,而做出的安抚江南读书人的手段。
南京大学堂,每年招生一千人,学习三年,毕业即可授官。
天下人都能看出,总督府之举,无疑是在向江南士子释放善意,招揽江南士子为其所用。
相比于南京大学堂的启用,大学堂旧址上的江南贡院,消失的无声无息。
江南贡院,始建于明景泰五年(1454年),是明清两朝举行乡试的场所,距今已经两百余年,想不到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
要知道,四年前,这里还操办过癸丑科的江南乡试。但随着战事扩大,义军攻破南京,占据江南,江南乡试遥遥无期,江南士子心急如焚,因为没有了科举取士,他们便失去了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机会,至于这天子是谁,是满是汉,他们并不在乎。
他们在乎的,只是能不能继续参加科举,飞黄腾达。
好在,科举的门虽然关上,南京大学堂的窗户却大开。
虽没了贡院,虽没了科举,但江南大学堂的创立与招生,无异于重开科举,而且,相比于科举三年一次,每科不过二三百人中举的比例,南京大学堂每年一千人的招生名额,实在太过欣喜。
但天下没有容易之事,南京大学堂也是如此。
最近一期的《江南日报》上,刊登了南京大学堂的招生简章,考取的科目包括数学、物理学、医学、地理等,在任何一科上有特长者,皆可优先入学堂。
而且,南京大学堂的考试科目中,还有体育,凡身体素质太差,不能通过考核者,不予录取。
最后一项,年龄三十五岁以下,更是让无数的江南士子惊呆。
光是这考核科目,年龄限制,就让涌入南京城的各地士子满腹牢骚,一片的反对之声。
八股文,以四书五经的八股化形式,为科举经义考试范围,阐释标准则以程朱理学为宗,南京大学堂的考核多是实学,这不是离经叛道吗?
以学堂代替科举,背离了历代取士之道,中华非华,世风不古,令人痛心。
西华门外,告示栏前,剃去辫子的士子们云集南京城,他们头戴网巾,身着汉家衣冠,埋怨的同时,一些人怀念起大清朝廷来,至少在那里,他们有一展身手,实现平生之志的机会。
“总督大人为诗词大家,通晓经史,为何要如此离经叛道,搞这些奇技淫巧之学?”
来自湖州府的陆肯堂长身玉立,折扇指着告示栏,摇头道。
“难道要我等脱去长衫,如那贩夫走卒,引车卖浆吗?”
海宁的陈元龙,同样是英俊白皙,出口抱怨。
“士农工商,自古以来皆然,我堂堂读书人习三教九流之学,士人的颜面何在?岂不是斯文扫地?”
溧阳士人黄梦群连连跺脚,愁容满面。
“如此斯文扫地,还不如当今朝廷!”
“离经叛道,武夫当政,必是不能长久!”
少数士子埋怨的同时,几个挎剑而过的年轻士子,却是停下脚步,均是面色愤愤。
“猪尾巴都剃了,狗还没有当够吗?”
“与其在这发牢骚,不如去武备学堂买些教材去学。只凭你那些狗屁八股文,能治国安民吗?”
“科举三年才两三百人,南京大学堂一年就是千人,还不知足吗?你们这些人,又几个能考中?”
挎剑者迎头痛斥,陆肯堂几人经纶满腹,本想反击,看到挎剑者胸口“江南武备学堂”几个字,都是闭口。
江南武备学堂,校长正是总督大人,学堂的学员都是总督大人的弟子,谁敢招惹?
况且,他们周围的许多士子,可是都在思量着,要是考不中南京大学堂,就去报考江南武备学堂。这个时候得知武备学堂,殊为不智。
“不知夷狄之辩,不懂春秋大义,心里只有功名利禄,还敢自称读书人,你们也配?”
“……余生则中华兮,死则大明,
寸丹为重兮,七尺为轻。
余之浩气兮,化为风霆;
余之精魂兮,变为日星。
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,垂节义于千龄……”
挎剑者冷冷抛下一句,几人大声《放歌》,扬长而去。
陆肯堂陈元龙等面红耳赤,一众士子都是沉默,无趣散开。
陆肯堂几人怏怏不乐离开,几人一路沉默,买了份报纸,进了一处酒楼。
“陆兄,南京的情形看起来不妙。难道我等要北上,去京城碰一碰运气?”
陈元龙低声道,小心翼翼打量着周围。
这里是南京城,总督大人的眼线不要太多,还是谨慎些,以免像刚才一样,被那几个武备学堂的学员羞辱。
“京城?”
陈元龙摸着茶杯,轻轻摇了摇头:“二位贤弟,你们不要忘了,咱们如今剪了辫子,一个个大光头,要是被那些旗人君臣发现,你们想过后果吗?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