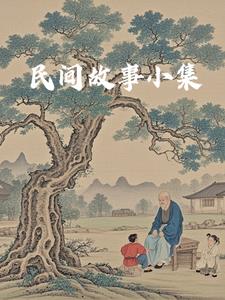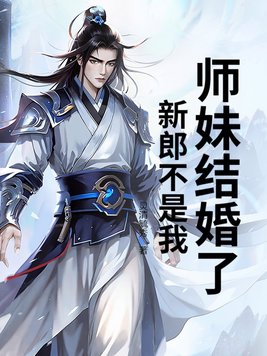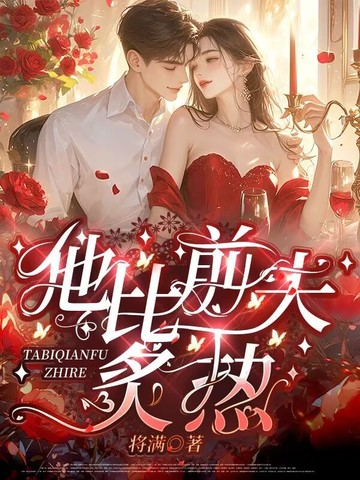在古老而静谧的清平镇,青石板路蜿蜒曲折,街边是错落有致的木质房屋,飞檐斗拱间透着岁月的痕迹。镇中百姓,多以务农或手工艺为生,日子过得平实而安宁。
孤女阿绣,就生活在这清平镇的一隅。她自幼父母双亡,靠着邻里的接济长大,为了谋生计,阿绣跟着镇上一位老绣娘学习刺绣。阿绣生得眉清目秀,眼眸中透着股倔强与聪慧,她心灵手巧,对刺绣有着极高的天赋,没几年工夫,便将老绣娘的手艺学了个十成十。
然而,阿绣的日子并未因此顺遂起来。同行们见她手艺精湛,绣出的花鸟鱼虫栩栩如生,仿若带着灵性,心生嫉妒,常常联合起来排挤她。在集市摆摊时,那些人会故意占去好位置,还散布流言,称阿绣的绣品虽看着花哨,实则用针粗糙,时日一久便会掉色变形。如此一来,阿绣的生意寥寥无几,生活愈发清苦,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居所也只是一间破旧的小屋,每逢雨天,屋内还滴滴答答地漏着雨。
这一年的春日,阳光暖融融地洒在清平镇的集市上,阿绣如往常一样,早早地来到集市一角,摆开自己的绣摊。她的绣品整齐地摆放着,有娇艳欲滴的牡丹手帕,振翅欲飞的蝴蝶香囊,还有灵动活泼的锦鲤摆件,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着她的心血,可路人大多只是匆匆瞥一眼,便移步他处。
临近晌午,集市上依旧人头攒动。阿绣正暗自叹息,忽然听到一阵喧闹声。她抬眼望去,只见一位老妇跌倒在地,周围的人虽多,却都只是驻足观望,无人上前搀扶。阿绣心下不忍,赶忙起身,快步走到老妇身边。那老妇头发花白,衣衫褴褛,面容憔悴,手中还紧紧攥着一根破旧的拐杖。阿绣轻轻扶起老妇,关切地问道:“婆婆,您没事儿吧?”老妇微微颤颤地站起身,拍了拍身上的尘土,感激地看着阿绣:“好孩子,多谢你啊,我这把老骨头,不中用咯。”阿绣见老妇并无大碍,便将她扶到自己的绣摊旁坐下,又从包裹里拿出干粮和水,递到老妇手中:“婆婆,您吃些东西,垫垫肚子。”老妇也不客气,接过干粮,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,看样子像是饿了许久。
待老妇吃完,阿绣又与她闲聊了几句,才知晓老妇是外乡流浪至此,无亲无故,身无分文。阿绣心中一阵酸楚,她想着自己孤苦伶仃的身世,对老妇的境遇更添同情。眼看天色渐晚,集市即将散去,阿绣收拾好绣摊,对老妇说道:“婆婆,您若不嫌弃,今晚可到我家中歇息一晚。”老妇眼中闪过一丝惊喜,连连点头。
阿绣带着老妇回到自己的小屋,屋内虽破旧,却被阿绣收拾得干净整洁。她找出自己的旧棉被,铺在木板床上,让老妇睡下。夜里,阿绣翻来覆去,想着老妇的遭遇,久久不能入眠。
第二日清晨,阿绣早早起床,准备了些简单的饭菜。老妇醒来后,看着忙碌的阿绣,眼眶不禁湿润了。用过饭后,阿绣又从自己不多的衣物中挑出一件相对厚实的棉袄,递给老妇:“婆婆,您在外漂泊,这春日里早晚还凉,您穿上这件衣服,暖和些。”老妇接过棉袄,手抚着衣料,哽咽着说:“好孩子,你这般善良,日后定会有福报的。”说罢,老妇轻轻拉起阿绣的手,阿绣只觉指尖似过电一般,微微麻了一下。老妇深深地看了阿绣一眼,又叮嘱道:“你要记住,善良之人,无论遇到何事,都莫要丢了本心。”阿绣虽心中疑惑,却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老妇告辞离去,阿绣望着她远去的背影,心中满是牵挂,却不知这一分别,日后竟还有奇妙的缘分。
自那老妇离开后,阿绣发现自己刺绣时仿若如有神助。以往刺绣,虽针法娴熟,但一些精细复杂之处,仍需耗费大量心力,如今针下的丝线却仿若有了灵智一般,自行穿梭游走。绣牡丹时,花瓣层层叠叠,娇艳欲滴,刚绣出几片,便能引得蝴蝶翩翩飞来,绕着绣架飞舞;绣锦鲤时,鳞片熠熠生辉,鱼鳍灵动飘逸,仿若下一刻便能跃入水中畅游。
阿绣的绣品名声渐渐在清平镇传开,起初,人们只是听闻有此等奇事,抱着好奇之心前来观看,可当亲眼见到那些绣品时,无不为之惊叹。订单也如雪花般纷纷飞来,阿绣从早到晚,忙得不可开交。看着生活逐渐有了起色,阿绣心中满是感恩,她知道,这或许是老天对她的眷顾,也是那老妇所言福报的开端。
随着生意越来越好,阿绣一个人愈发忙不过来,便想着收个徒弟。一日,她在集市采买刺绣材料时,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,那是个小男孩,衣衫破旧,脸上脏兮兮的,手中正拿着一个馒头,拼命往嘴里塞,看样子饿极了。阿绣心中一动,走上前去,轻声问道:“孩子,你叫什么名字?父母呢?”小男孩抬起头,眼中满是警惕与防备,过了好一会儿,才小声说道:“我叫小豆子,我没有父母,他们都死了。”阿绣心疼不已,她摸了摸小豆子的头,说:“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走,我教你刺绣,以后有饭吃,有地方住。”小豆子眼中闪过一丝惊喜,随即又有些犹豫,阿绣看出他的心思,笑道:“放心,我不会亏待你的。”小豆子终于点了点头,跟着阿绣回了家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